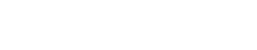
0763-1166-2098
NEWS
新闻资讯


发布时间:2025-11-11 点击量:
创作声明:本文为虚构创作,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,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,仅用于叙事呈现,请知悉
开国皇帝朱元璋,这位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铁腕君主,刚刚失去了他一生唯一的挚爱——马皇后。
他将自己幽闭于深宫,而在马皇后病逝的那个凄冷的夜晚,他却下达了一道让整个皇城为之震栗的密令。那道旨意,对准的不是别人,正是马皇后生前最信任的近侍,陈福。
在那个权力与悲伤交织的顶点,紧闭的佛堂门后,究竟发生了什么,能让一个鲜活的人,无声无息地沦为活着的幽魂?

洪武十五年的秋天,应天府的梧桐叶还没来得及落尽,大明朝的国母,马皇后,就先一步凋零了。
坤宁宫里,悲伤像是一场无声的落雨,浸湿了每一寸雕花的廊柱,每一匹云锦的幔帐。那些平日里争奇斗艳的宫女太监,此刻都跪在地上,哭声此起彼伏,有几分真,几分假,谁也分不清。哭,是此刻唯一正确的事。
他跪在马皇后的灵床边,手里攥着一块半干半湿的布巾,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张曾经无比熟悉,此刻却冰冷僵硬的脸。他的动作很轻,轻得仿佛怕惊扰了一个沉睡的人。从额头到脸颊,再到下巴,每一个角落他都擦得仔仔细细。这是他二十年来每天都要做的事,只是今天,他手里的布巾是温的,可娘娘的脸,却是怎么也捂不热了。
悲伤并没有化作眼泪从他眼眶里涌出,而是凝结成了冰,冻住了他的四肢百骸,顺着僵硬的指尖,传递到那块布巾上。
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膝盖已经跪得麻木,也听不见殿外那些震天的哀嚎。他的世界里,只剩下他和床上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的女人。
陈福不是天生就该在这宫里伺候人的。他的记忆里,有过阳光,有过泥土的气味,还有过一种叫“饿”的感觉。那是濠州大饥荒的年头,他才七岁,爹娘都倒在了逃荒的路上。他就趴在死人堆里,像一只被丢弃的小野狗,等着自己的身体也慢慢变冷。
就在他以为自己就要被野狗分食的时候,一双穿着布鞋的脚停在了他面前。他费力地抬起头,看到一个面容温柔的女人,她的脸颊也因饥饿而凹陷,可眼神却亮得像天上的星星。
她掰了半个黑乎乎的杂粮馍,塞进了他干裂的嘴里。那馍又干又硬,剌得他喉咙生疼,可他至今都记得,那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
是她,把他从死人堆里刨了出来,给了他一命的吃食。为了能一直待在这份温暖的旁边,为了报答这份比天还大的恩情,当他们安定下来后,陈福做了一个让他成为“陈福”而不是“张三李四”的决定。
他求了人,净了身,进了王府。从此,世界上少了一个可能饿死的野小子,多了一个叫陈福的太监。他的一辈子,就浓缩成了两个字——“娘娘”。
“福公公,灵堂那边都备妥了,您看……”一个管事太监猫着腰,小心翼翼地凑过来。
陈福像是没听见,他的目光落在了皇后手边的一个梳妆盒上。他打开盒子,里面是一件件他再熟悉不过的首饰。他拿起一支通体翠绿的玉簪,这是娘娘嫁给皇爷时,皇爷用身上仅有的几块碎银子换来的,成色并不好,上面还有个小小的缺口。可娘娘宝贝了一辈子,只有在最要紧的日子才舍得戴上。他又拿起一副珍珠耳坠,这是皇爷登基后第一次南巡,从海边带回来的,说是东海的鲛人泪,能保佑平安。
陈福将这些东西一件件拿起,又一件件轻轻放下。每一件物品,都牵连着一段旧时光。那些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,冲刷着他那颗早已被悲伤冻住的心。
宫人们在底下忙碌着,窃窃私语。大家都在担心,都在害怕。皇爷还没露面。谁都知道,这位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开国皇帝,心里唯一的软肉,就是这位马皇后。如今这块软肉被活生生剜掉了,这头老虎,会咬死多少人来泄愤?
陈福不关心这些。他只知道,娘娘走了,他的天,塌了。他唯一的念想,就是把娘娘的遗物都整理好,别让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给偷了去。就在他拿起一个看起来很寻常的雕花小木匣时,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笼罩了他。
他没有穿那身象征着九五之尊的龙袍,身上只是一件半旧的藏青色常服,领口还沾着些许灰尘。他的头发有些散乱,那双在朝堂上足以让百官胆寒的眼睛,此刻布满了蛛网般的血丝。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皇帝,更像一头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,被逼入绝境的孤狼。
他的目光没有落在灵床上一动不动的妻子身上,也没有理会跪了一地的宫人。那双鹰隼般的眼睛,穿过昏暗的烛光,越过缭绕的香烟,死死地、死死地钉在了陈福和他手里的那个木匣上。
那眼神里,没有痛失爱妻的悲痛,没有一丝一毫的哀伤。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、偏执的、要将一切吞噬的占有欲。那眼神让陈福浑身一颤,手里的木匣差点掉在地上。他从未见过皇爷这般模样,仿佛那个木匣里装着的,不是什么首饰,而是他失落的魂魄。
坤宁宫外,按制式搭建的灵堂灯火通明,白幡在夜风中无力地飘荡。文武百官按品级跪在外面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按照祖宗的规矩,皇帝要在灵前守满七天七夜。这是为人夫,也是为一国之君的本分。
可朱元璋却把自己关在寝殿里,一整天了,水米未进。谁去劝,谁就挨一顿臭骂。大殿内外,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前的死寂。
陈福已经将皇后的遗物尽数整理入册,封存妥当。他默默地退到角落,像个没有情绪的木偶,等着下一个指令。他知道,等丧仪开始,他就再也不能这样近地守着娘娘了。
所有人都以为皇帝是要去灵堂了,纷纷低下头,准备听候差遣。可朱元璋却径直走到了陈福面前。
陈福的心猛地一揪,这是皇爷今天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他垂下头,恭敬地回道:“回皇爷,奴婢自十三岁起便跟着娘娘,到如今,整二十年了。”
“二十年……”朱元璋低声重复了一遍,像是在咀嚼这两个字的分量。他点了点头,眼中那股无人能懂的狂潮再次翻涌起来。他转过身,对着门口的总管太监黄俨,下了一道让殿内所有人血液冻结的口谕。
“传朕旨意,”他的声音不大,却像一把冰锥,刺进每个人的耳朵里,“将坤宁宫近侍陈福,锁入西苑佛堂,无朕的命令,任何人不得探视,不得开门。”
所有人都懵了。他们设想过无数种可能,皇爷或许会大开杀戒,或许会迁怒御医,或许会罢朝几天。可谁也没想到,他第一个要处置的,竟是马皇后最信任、最忠心的近侍陈福。
众人立刻脑补出无数种可能。难道是陈福伺候不周,导致娘娘病情加重?难道是陈福冲撞了皇爷,说了不该说的话?甚至有人恶意地猜测,是不是这个奴婢知道了什么皇家秘辛,皇爷要杀人灭口了?
黄俨也是一愣,但他不敢多问,立刻应了声“嗻”,招了招手。两个身材高大的禁卫立刻走了进来,一左一右,像拎小鸡一样架住了陈福的胳膊。
陈福整个人都傻了,他完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。他的大脑一片空白,只能任由禁卫将他往外拖。他的目光越过所有惊诧、怜悯、幸灾乐祸的脸,最后落在了朱元璋的背影上。那背影依旧挺拔,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孤寂和决绝。
他的嘴唇翕动着,却一个字都问不出来。因为他知道,皇帝的决定,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。
这里是马皇后生前用以念经祈福的地方,平日里除了她和几个洒扫的小太监,几乎无人踏足。佛堂不大,却收拾得一尘不染。空气里,还隐隐残留着娘娘最喜欢的那种,从域外传来的老山檀香的味道。
身后那扇厚重的楠木门被无情地关上,紧接着是铜锁落下的沉重声响。这声音,像一把大锤,狠狠砸在了陈福的心口上。他腿一软,瘫坐在了冰冷的石砖地上。
他慢慢抬起头,环顾四周。佛堂的陈设简单至极,正中央供着一尊白玉观音,观音像慈眉善目,手持净瓶,悲悯地俯瞰着众生,也俯瞰着此刻像丧家之犬一样的他。观音像前,是一张红木长案,上面摆着几卷摊开的佛经,一个铜香炉,和一盏长明灯。
那盏灯的灯芯结了小小的灯花,昏黄的光晕在佛堂里投下斑驳的光影,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孤零零地映在墙壁上。
如果皇爷是要降罪于他,为何不送他去慎刑司?那里有的是让人开口的法子。如果皇爷是要他死,为何不直接赐他三尺白绫?那更干净利落。
难道……是娘娘临终前,对他有什么不满,托付给了皇爷?陈福的心揪了起来。他跪直身体,挪到观音像前的蒲团上,开始发疯似的在脑子里回忆。娘娘病重的那段日子,他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?哪碗药端得迟了?哪件事做得不合心意了?
他想了很久很久,想得头都疼了。他能想起来的,只有娘娘拉着他的手,气若游丝地嘱咐他:“阿福啊,我走了以后,你要好好伺候皇爷。他那脾气,你晓得的……没人看着他,我……不放心……”
想到这里,陈福的眼眶终于红了。他死死咬着嘴唇,不让那滴就要夺眶而出的眼泪掉下来。娘娘,您看,您不放心的人,现在要把奴婢给锁死了。
外面的世界仿佛消失了。风声,虫鸣,远处隐约的哭丧声……所有的一切,都被这四面墙壁隔绝在外。佛堂里静得可怕,只有那盏长明灯在燃烧时发出的、微不可闻的“噼啪”声。
陈福从最初的惴惴不安,到后来的胡思乱想,再到最后的彻底绝望。他觉得,自己就像一个被主人遗忘在角落里的旧物件,静静地等待着发霉、腐烂。
他看着那尊观音像,看着那些佛经,看着这满室熟悉的陈设。他觉得,或许皇爷并不是要惩罚他。或许,这是皇爷对他的一种考验,考验他对娘娘的忠心。
他站起身,走到墙角,拿起那把娘娘生前用过的抹布和木桶。他打来清水,拧干抹布,开始一丝不苟地擦拭起来。先是佛像的底座,然后是供桌的桌腿,再到每一本经书的封面。他的动作很慢,很仔细,仿佛这不是在干活,而是在完成一种神圣的仪式。
这是他唯一会做,也唯一能做的事了。只要让他做这些跟娘娘有关的事,他的心,就是定的。
佛堂外,两个奉命看守的禁卫笔直地站着,像两尊铁塔。他们竖起耳朵听了半天,里面除了刚开始有点动静,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。连一声咳嗽,一声叹息都没有。
“你说,这陈公公在里头干啥呢?”一个年轻点的禁卫忍不住,压低声音问旁边的同伴。
“谁知道呢。”年长的那个禁卫目不斜视,“不该问的别问。皇爷的心思,是咱们能猜的?站好你的岗,小心隔墙有耳。”
年轻禁卫缩了缩脖子,不敢再作声。可宫里早已炸开了锅。太监们三三两两聚在背光处,交头接耳。
“听说了吗?陈福被锁进西苑佛堂了!”“我的天,这节骨眼上?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?”“我猜啊,肯定是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。你想想,娘娘临终前,就他一个人贴身伺候……”“不对不对,我听说是皇爷悲伤过度,想找个人给娘娘殉葬,拿他开刀呢!”
各种版本的猜测,一个比一个离奇,一个比一个惊悚。这个本就因国丧而悲伤的夜晚,因为陈福的被囚,更添了几分诡谲不安的气氛。

两个禁卫心头一凛,这脚步声他们再熟悉不过了。他们立刻跪倒在地,头也不敢抬。
朱元璋的身影出现在了月光下。他挥了挥手,示意两个禁卫退下。禁卫如蒙大赦,连滚带爬地退到了远处。
朱元璋独自一人,走到了佛堂门口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黄澄澄的铜钥匙,那是开启这扇门的唯一钥匙。他将钥匙锁孔,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“咔哒”声,那把沉重的铜锁被打开了。
整整一夜,再也无人靠近那座与世隔绝的佛堂。谁也不知道,在那扇紧闭的门后,在大明朝的皇帝和他妻子最信任的近侍之间,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第二天清晨,当第一缕熹微的晨光,费力地穿透应天府上空的阴霾,照在西苑佛堂的琉璃瓦上时,那扇紧闭了一夜的门,终于开了。
仅仅一夜之间,这位大明朝的皇帝,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,凭空老了十岁。他眼窝深陷,脸色是灰白的,那双曾让无数人胆寒的眼睛里,此刻只剩下一种燃烧殆尽后的空洞。他身上的常服皱皱巴巴,藏青色的下摆处,还沾着一些白色的、像是香灰一样的粉末。
他没有说一句话,甚至没有看任何人一眼,就那么迈着沉重的步子,径直朝着大殿的方向走去。他的背不再像昨日那般挺拔,微微佝偻着,像一座被风霜侵蚀了千年的石像,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萧索。
皇帝的身影消失在宫墙拐角后,两个小太监才敢壮着胆子,走进佛堂。片刻之后,他们一左一右,将陈福架了出来。
他整个人就像一具被抽走了魂魄的木偶,被两个小太监拖着走,双腿绵软无力。他的脸白得像一张纸,那双往日里总是温和而恭顺的眼睛,此刻涣散无神,看不到一丝光亮,仿佛透过眼前的一切,在看一个无人能懂的、虚无的远方。
一个与陈福相熟的老太监,是马皇后宫里的老人了,见状连忙跑上前扶住他,急切又关切地问:“福公公!我的老天爷,你……你没事吧?皇爷他……他没把你怎么样吧?”
他张大了嘴,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,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像是破旧风箱被拉扯时发出的“嗬……嗬……”的气音。

老太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,脸上的关切瞬间变成了惊恐。架着陈福的两个小太监,也吓得手一松,陈福便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上。
一夜之间,一个活生生的人,一个前一天还能清晰回话的人,就这么变成了哑巴。
这个消息,比昨天他被囚禁的消息,更具爆炸性,像一场无形的瘟疫,以令人咋舌的速度传遍了整座紫禁城。
这比任何酷刑都让人感到恐惧。打一顿板子,身上有伤;挨一顿烙铁,身上有疤。可现在,陈福身上完好无损,却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。皇爷在那间小小的佛堂里,到底对他做了什么?用了什么神仙鬼怪般的法子,能让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就变成了哑巴?
他没有被送回坤宁宫,也没有被送去任何显眼的地方。他就那么被安置在了皇城一角,一间最偏僻、最潮湿的杂役房里。那里住的,都是些老得干不动活,只等着出宫或者等死的老太监。
从此,他成了一个活着的幽灵,一个行走的禁忌。宫人们远远地看见他,都像见了鬼一样绕着走,生怕他身上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“晦气”沾染了自己。
夜里,他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,拼命地想要说话,哪怕只是叫一声“娘娘”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嘶吼,去呼喊,可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大团浸了水的棉花,除了发出一些让他自己都感到害怕的、野兽般的嘶鸣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梦里,他又回到了那间昏暗的佛堂。他又看到了皇爷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。皇爷的嘴在动,在对他说着什么。他拼命地想看清皇爷的脸,想听清皇爷的话。可每当他要看清的那一刻,梦境就化作无数碎片,他会猛地惊醒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浑身被冷汗浸透。
然后,他会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喉咙,试着发声,可结果依旧是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无边的恐惧和绝望,像疯长的藤蔓,将他一层又一层地紧紧缠绕,让他透不过气来。他想不通,那一夜之后,他的声音,究竟去了哪里?
陈福不再挣扎着想要说话了。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,像一只受伤的蜗牛,缩回了自己坚硬的壳里。他每天做的,就是坐在杂役房门口那块小小的石阶上,呆呆地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,从翠绿,到枯黄,再到被秋风一片片卷走。
他的世界里,再也没有了声音。于是,那些被封存的记忆,便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,在他的脑海里反复上演。
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,他刚进王府没多久,因为手脚笨,打碎了管事的一个茶杯,被罚跪在雪地里,不准吃饭。雪花落在单薄的衣服上,很快就融化了,刺骨的寒意顺着膝盖往骨头缝里钻。他饿得眼冒金星,觉得自-己可能就要这么冻死、饿死了。
就在他意识模糊的时候,一双温暖的手,给他披上了一件带着体温的厚棉袄。他抬起头,看到了马氏那张温柔的脸。
“起来吧,地上凉。”她的声音总是那么柔和,“人又不是瓷器,哪有不犯错的。快,趁热吃了,暖暖身子。”
她递给他一个还冒着热气的烤红薯。那红薯的香甜,驱散了他身上所有的寒冷。也就是从那天起,他被调到了她的身边,专门伺候她。
她会耐心地教他识字。她握着他的手,一笔一划地在沙盘上写下他的名字。“陈福,陈福,”她笑着说,“你看,这是你的名字。人有了名字,就不是无根的草了。”
她会教他分辨草药。后院里,她开辟了一小块药圃,种满了各种草药。她会指着一株植物告诉他:“这个叫蒲公英,瞧着不起眼,却是清热解毒的好东西。这世上的东西,跟人一样,不能光看外表。”
当他被其他资历老的大太监欺负,克扣了月钱时,他不敢说。可她却能一眼看出来。她不会大张旗鼓地去责罚谁,只是会在第二天吃饭的时候,当着朱元璋的面,轻描淡写地说一句:“重八,咱们府里是不是缺钱了?我瞧着福儿这孩子,脸都饿瘦了一圈。再苦,也不能苦了身边的人啊。”
朱元璋当下便会明白,转头就把那个管事太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从此,再没人敢轻易招惹陈福。
在陈福心里,娘娘不仅是他的主子,是他的恩人,更像是他从未有过的亲人,是姐姐,是母亲。他这条命是她给的,他所拥有的一切,都是她赐予的。所以,为她做任何事,他都心甘情愿。
他记得最清楚的,是有一回,朱元璋在外打了胜仗,却因为一个将领冒进损兵折将而大发雷霆,要把那人拉出去砍了。满屋子的人都跪在地上求情,朱元璋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
眼看那将领就要人头落地,马皇后却不慌不忙地让陈福端了一碗刚炖好的鸡汤进去。
她把汤递给朱元璋,柔声说:“重八,先喝口汤,暖暖身子。你看这汤,滚烫滚烫的,要是急着喝,非把嘴烫坏了不可。得等它慢慢凉下来,才能品出味道。这治理军队,跟喝这碗汤不是一个道理吗?将领有错,是该罚,可要是把人杀了,以后谁还敢为你带兵打仗呢?凡事,都不能太急。”
朱元璋听了这番话,愣了半晌,最后长叹一口气,把那碗汤喝了,也收回了成命。
这就是娘娘的智慧。她从不用强硬的方式去对抗皇爷那暴烈的脾气,而是像水一样,用最温柔的方式,去化解那百炼的钢铁。她是皇爷唯一的“刹车”,也是他唯一的精神港湾。
后来,他们入主应天府,成了天底下最尊贵的人。娘娘还是跟以前一样,吃的穿的,都极尽简朴。她常常对陈福说:“福啊,咱们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,不能忘了本。如今锦衣玉食,更要惜福。”
她带着宫人们纺纱织布,把织好的布匹赏赐给大臣的家眷。她说,这不光是为了节俭,更是为了让那些官太太们知道,一丝一缕,皆来之不易。
最后的那些日子,娘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她躺在病床上,咳得撕心裂肺。陈福衣不解带地守着她,心也跟着一揪一揪地疼。
她吃不下东西,他就想尽了法子,把山珍海味都换成最普通的米粥,用小火慢慢地熬上几个时辰,熬到米粒都化开,再一勺一勺地喂给她。
她夜里疼得睡不着,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,给她讲小时候在濠州街头听来的那些笑话和故事。尽管那些故事他讲了无数遍,自己都觉得乏味,可娘娘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。
临终前的那一天,她的精神忽然好了很多。她把陈福叫到床前,拉住他的手,那只手已经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了。
她喘着气,断断续续地说:“福啊……我这一辈子,没什么放不下的……就是皇爷……他那脾气……我走了,就没人能劝着他了……你……你是个稳重的孩子,你要替我……多看顾着他……别让他……做了糊涂事……”
陈福跪在地上,泪流满面,一个劲儿地磕头:“娘娘您放心,奴婢记下了!奴婢拿命记下了!”
可现在,奴婢成了一个哑巴。一个连话都说不了的废人,要怎么去完成您最后的托付?
这三年里,大明朝的天,变得越来越阴沉。没有了马皇后的约束,朱元璋的猜忌心和铁腕手段愈发登峰造极。朝堂之上,但凡有半点忤逆之声,轻则罢官流放,重则人头落地,株连九族。开国功臣们一个个如履薄冰,整个应天府都笼罩在一股压抑而血腥的气氛之中。
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,也是最钝的磨刀石。他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无声的生活,习惯了旁人躲闪的目光,习惯了终日的沉默。他不再做噩梦,也不再为自己无法说话而感到绝望。他就那样活着,像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一样,静默地迎接着每一个日出和日落。
无论春夏秋冬,他的双手,都永远缩在宽大的衣袖里,从不轻易示人。吃饭时,他用勺子;干活时,也尽量用胳膊肘去使力。那双曾经为马皇后调羹试药、穿针引线的灵巧的手,仿佛成了他身上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这年冬天,宫里新选了一批小太监。其中一个叫宝生的,因为年纪小,又没什么眼力见,被管事太监嫌弃,打发到这没人愿意来的杂役院,负责给陈福这些“老废物”送饭。
宝生才十四岁,还带着乡下孩子的质朴和天真。他不害怕宫里那些关于哑巴陈公公的恐怖传言,反而觉得这个总是默默坐在石阶上、眼神空洞的老太监很可怜。
“陈公公,今天天冷,我给您多打了点热汤,您趁热喝。”“陈公公,您看,今儿出太阳了,暖和和的,您多坐会儿。”
陈福从不回应,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可宝生不介意,他觉得,哪怕只是自己说,也能给这死气沉沉的院子添点活人的动静。
这天,应天府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。雪不大,薄薄的一层,给院子铺上了一层银白。
宝生提着食盒过来的时候,看到陈福正拿着一把大扫帚,在院子里吃力地打扫着落叶和积雪。他的动作很笨拙,因为他始终不肯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,只是用两个手肘夹着扫帚柄,一下一下地往前推。
就在他靠近的一刹那,一阵穿堂风猛地吹过,卷起了地上的雪沫,也吹起了陈福那宽大的衣袖。
他看到了陈福的手腕。那手腕上,有一圈深紫色的、极其怪异的淤痕,像被粗麻绳狠狠捆绑了很久很久,已经渗进了皮肉里,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褪去的印记。
他的双手,十根手指的指尖,竟然全都是平的!那上面没有指甲,一-片光滑的指甲盖都没有!取而代之的,是一层蜡黄的、凹凸不平的、看起来像盔甲一样坚硬的角质层。
那根本不像一双人手,倒像是某种兽类的爪子,在石头上磨了千百遍之后的样子。

联系我们
Contact us
SERVICE TIME:08:30-18:30